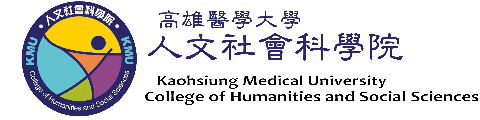這學期的解剖課程中新加入了一項被稱為「跑台」的考試。這門課程的上課方式很特別必須穿著實驗衣,戴著醫護人員會戴那種纖維口罩,進入一間擺放著數床大體的教室,細讀一個個肉身故事。
記得這學期第一次進入大體實驗室時並沒有太多忐忑,也許是高中時期參加過大學營隊看過大體的緣故,對大體老師並不會感到害怕。
記得學期初剛進入大體室時,福馬林味瞬間以侵略之姿全面進攻我的鼻腔,緊接下來實驗室中的低溫如毛毯般將我環繞覆蓋,讓我同 時打了個鼻涕和一身寒顫。
手術台上的肉身以綠色塑膠包裹外層還有藍色薄膜掩覆。一個個著白袍的臉被口罩遮掩以至於分不清誰是誰的同學們圍繞於手術台, 老師一聲令下要我們將大體老師翻身好觀察背部肌肉。
同組的我們都為女生,起初大夥面面相覷不知道該如何下手。愣了幾秒,幾個女生(包括我)怯怯地伸出手試圖將壯碩的大體老師翻 面。幾個人七手八手,一些手扶老師的左肩,一些手撐住右邊臂膀, 幾位同學從背部推。我傾身幾乎貼近冰冷的肉體,感受到更低於周遭的氣溫臉上竄。突然間我發現自己竟然微微顫抖。
終於將老師翻面過來,層層掀開了塑膠布。不曉得是我的錯覺還是真如此,我感覺到周遭的女孩們在深褐色肉色與肌理顯露出來的瞬間,輕微的退後了。口罩遮掩了她們的表情。
在一次又一次課堂的講解中,繁雜的神經血管與界限不明的肌肉組織漸漸抹淡了大家對大體老師些許的恐懼,同學們很快就熟練地拉起一條條血管討論其正確的名字,也能談笑著說出:「喔~原來我們身體裡面就是長這樣啊」的這種話。
儘管如此,難免還是有人不習慣。據說就有同學一個禮拜不想吃肉只吃吐司。但我倒沒有這個困擾,幾次還在大體實驗室的隔壁教室 吃午餐完全不受影響。也許我是個奇怪的人吧。
還有不曉得為甚麼,我的目光總是會被大體老師的臉部吸引,接著便會陷入無止盡著迷似的凝視。掀開的臉部皮膚露出底層泛白的肌 肉纖維與數罟的血管神經,緊閉的雙眼與唇深深的印刻出臉部的線條 與溝痕,短而剛的細毛扎於皮層不時摩擦到手產生粗糙的觸感。我總 感覺得出他們那種想說甚麼卻又無法言語的情緒,而臉部表情就這麼 定格在那裏,彷彿被時空凝滯。
於是我的思緒飛到了教室外的祈福板上,每位老師離開前要留給 這個世界的故事。上面的每個故事內容不外乎就是老師簡單的生平介紹、畢生經歷與得病經過,離走前選擇捐贈大體的大愛之情則作為結尾。
我不曉得人終其一生,該用多少字撰寫才能寫出生命中的那些喜怒哀樂,那些五光十色,那些波濤洶湧,與那些刻骨銘心。也許一些 人需要長篇大論加以敘述其高潮迭起的生命歷程;但我相信也有些人 只需要幾句話就能道盡終生而沒有遺憾。人想在死亡後留下怎樣的故 事,端看他想用甚麼姿態讓後人緬懷與追憶。 有肉體才有故事的存在,但是故事完整了一個人。儘管殘破的肉體 留下了曾經活過的具體證據,屬於靈魂歸屬的故事卻硬生中斷。
今年的清明連假全家依慣例回南投掃墓。 位在南投某山處的大型公墓祭祀地點有座靈骨塔,往年都是父親阿嬤進去祭拜。今年我說我也想進去看看,沒有被阻止。 隨父親走上二樓,大片牆面延伸至天花板都是放置骨灰罈的鐵隔讓人猛然產生被置物櫃包圍的幻覺。 走到某處父親打開鐵櫃鎖,向裡面的骨灰罈拜了一拜。
「這是阿公。」 我端詳著那個莫約半公尺高的大型骨灰罈,餘角看見父親口中唸唸有詞。當下的我並沒有太大的衝擊,因為一個大型花瓶般的陶瓷品並不能讓我對一個「真實的人」產生連結,但看見父親與阿嬤、、、不對,應該是說看見在場所有誠心膜拜的人,隱隱間我總覺得這些已 經脫離肉體的人們仍在這些後輩口中傳頌與記憶,被訴說著關於生前 的點點滴滴,被一而再的懷念著。他們無所不在,如影隨行。
這是不是也是另一種方式活下來的方式?活在別人的記憶中。
期中考週大體教室充滿著準備考解剖的同學們,每床大體四周都 圍繞著一群著白實驗衣的同學。大體教室頓時熱鬧滾滾陽氣興盛。
看見這幅場景我突然想到曾看過一幅世界名畫叫「杜爾博士的解 剖學課」。畫中一位教授從容自若的夾起一絲肌肉講解,一群學生神情專注聚精會神的聆聽著,在翻飛的肌理血管組織中,彷彿齊聲朗誦一個個肉身故事。
瞬間那幅畫與眼前場景重疊,我不禁會心一笑。